
前幾個月在衛視西片台看【小太陽的願望】時,發現其中一句台詞「Welcome to hell」被翻成「歡迎來到杜鵑窩」。我實在不懂為什麼要自作聰明擅作主張翻出一個故作文雅卻沒人懂的詞彙?尤其是劇中角色還把這句話大大的寫在紙上,不需要很優的聽力就能了解他想表達什麼,卻看到意思完全不同的翻譯,不但覺得該有的笑點莫名的卡住了,還得花時間去疑惑到底什麼是他媽的杜鵑窩?
就這樣辜狗了一下,才知道原來杜鵑窩為精神病院的隱喻(但仍無法原諒譯者亂吊書袋),也從而得知【飛越杜鵑窩】這部在1975年囊括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導演及最佳改編劇本獎項的經典之作。
(以下是不傷大雅的小雷)
傑克尼克遜飾演的麥克墨菲是個「工作怠惰、未經允許就發言」的無賴中年男子,被送進精神病院觀察。院裡有口吃的年輕人、不停跳著華爾茲的老人、智商很低的啞巴印地安「酋長」......有些人是被送進來的,有些人卻是自願進來的。他們不見得真的有病,但都有不願被觸及的過去,寧願在院中喝不知效用的藥水、被逼迫將傷疤重新挖開攤在眾人面前檢視,卻不願走出去活在現實當下。
麥克墨菲出現之後,質疑當權護士長的作法、試圖改變院內的氣氛,也將對生活的熱情感染到周圍的病友身上,讓原先不敢反抗的他們逐漸敢夢想、敢要求。這些挑戰權威的行為導致雖然已被醫生判定沒有病,卻也無法回到外面的世界,反而被施以電擊治療強迫他聽話。
(以下大雷,請斟酌享用)
他不斷嚐試逃跑,第一次失敗了,但他說「至少試過了」;第二次他騙過護士開走醫院的巴士,載了整車的病人出海體驗活著的真實感,然後等著再被抓回去蹲;第三次他下定決心要離開,鑰匙拿到手了,鐵窗也開了,來接他的車已經停在外頭,最後卻因為捨棄不下這群病友而錯失大好良機。然而這次等著他的懲罰不是電療,而是以手術刀破壞他大腦的前額葉,讓他從一個只是不守社會規範的正常人,變成貨真價實的神經病。
終究是要一方犧牲才能換取另一方覺醒。護士長重新掌控局面,院內的秩序恢復,病友們以為只是做了一場可以突破的美夢。夜裡,一直沒有勇氣面對自己人生的「酋長」,對著沒有意識的麥克墨菲承諾不會將他獨自留下,接著打破窗戶,帶著他解脫了的靈魂,奔向自由。那一刻,病友們從睡夢中醒來,帶著希望的狂喜不斷呼喊麥克墨菲的名字,直到酋長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
人們羨幕的、極力追求的特質往往是自己身上缺乏的,我想也是。離十八歲越遠,越害怕自己逐漸向世故靠攏、向權力屈服,因此我無法不被那些無視規範、坦率地追求渴望的人們吸引。然而就像酋長其實並不是沒有能力破窗而出,只是要或不要的選擇題,我其實可以不必羨慕別人。如果我們都被困在一起,選擇成為被困住的正常人,或是被困住的神經病,其實沒什麼不一樣。能不能有第三種選擇?不試試看怎麼知道?
用力感受這個世界,不要輕易讓感覺麻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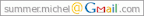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